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56年,大宋嘉祐元年,大辽清宁二年。
怪了!去年大辽还是重熙二十四年,怎么今年就成清宁二年了,元年哪去了?
对呀,去年八月,辽兴宗去世,辽道宗即位,1055年当年就改了年号,重熙二十四年也是清宁元年了。
大宋这边,宋仁宗也换年号了,从“至和”改成了“嘉祐”。祐这个字,专指天神的护佑。
宋仁宗一共用了9个年号,很多次改年号,都是因为天灾。第一次,从“明道”改元“景祐”,是因为当时连年旱灾,求老天爷保佑;第二次,从“庆历”改元“皇祐”,也是因为当时连年旱灾,继续求保佑;而这一次,大宋改元“嘉祐”,是因为水灾。从这一年的五月开始,连天暴雨,在都城开封,水把城门都冲垮了,好几万栋房子都被毁。
这么大灾情,光改年号也不够,还得有其他表示。仁宗皇帝发下一道诏书,先是做了自我批评,都怪朕不好。要不大家都说说?看看那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我改还不行吗?
人群中闪出一位,不是别人,正是咱们的老熟人欧阳修。他这次提的意见,是撤掉一个人,老天爷就不下雨了。谁啊?狄青,北宋的名将,现任主管国家军事的枢密使,前两年平定侬智高叛乱的大功臣狄青。那为啥撤掉他就不下雨了呢?肯定是一套我们今天听起来是歪理儿的说法。欧阳修说,您看,下雨就是水嘛,水在阴阳里属阴,兵呢,也属阴,武将呢,也属阴。老天爷的示警,从来不会搞错的,下雨就是让您撤换武将狄青。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的逻辑,当时确实是可以这么聊天的。
当然了,欧阳修也有严肃的理由,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武将掌管国家的最高军情机密,还深得军心,不是啥好事。你懂的,这是宋朝崇文抑武的老腔调。欧阳修还算厚道,把另一个角度的话也说了,现在罢狄青的官儿,既是为国家好,也是保全他,为了他好,等等。
这次看来是约好了,除了欧阳修,还有几个大臣,都一齐出手,要求朝廷罢免狄青。而他们下手就比较重了。比如范镇就对宋仁宗说,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一场兵变马上就要发生,老臣我与其让乱兵砍死,还不如死在谏官的任上,您要再不听我的建议,干脆把我杀了算了!情绪这么激动,是不是有点夸张?
还有更狠的,说,狄青家的狗,头上长出犄角,还有人看到狄青家里有红光。还有,前面不是说这一年开封城发大水嘛,狄青把全家搬到了一座寺庙里。有人说亲眼看到,狄青穿着黄色衣服,坐在寺庙的大殿上指挥士兵。哎,你们不如直接说狄青要造反当皇帝得了。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没底线的造谣陷害了。
到了这一年的八月,宋仁宗实在扛不住了,只好罢了狄青的枢密使,安排到了陈州(今河南周口)当知州。然后,也就半年的功夫,狄青就在陈州忧惧而死。

听到这儿,你可能已经怒发冲冠了。对啊,这不就是南宋岳飞的故事在北宋的预演吗?跟岳飞一样,狄青也是战功赫赫,也都深受士兵的爱戴和皇帝的器重,也曾被提拔为枢密院的长官,又都遭受了朝廷的迫害。
但是,狄青和岳飞的故事,还有一个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狄青的故事里没有秦桧。秦桧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派,永世不能翻身。可是站在狄青对面的呢?欧阳修、范镇,还有其他几位,都是一代名臣。
这就让我们有点为难了。一个没有反派的故事不好讲。迫害英雄、毁我长城这种事,到什么时候都是一种恶行吧?为什么这些士大夫们就忍心为之?而且还是一批号称正直的士大夫呢?
那这狄青罢官的事件,是文官士大夫抱团围攻、挤兑武将?还是宋朝那种根深蒂固的“崇文抑武”的政治传统突然恶性发作?好,这一期《文明之旅》节目,我们就来看看英雄狄青的故事,为什么注定是一场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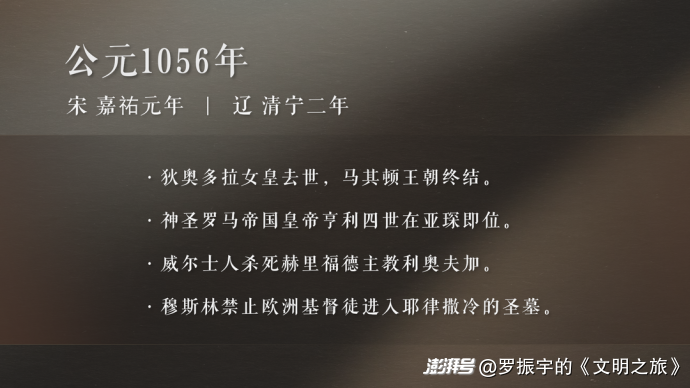
枢密使狄青
为什么大宋的这些名臣要和狄青过不去?非要把他从枢密使的位置上拉下来?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大宋朝根深蒂固地不相信武将。五代时期留下来的教训太深刻了,武将一旦得了高位,就有可能造反,就会带来恐怖的乱世。
但是,具体到狄青担任的枢密使这个官职,事情又没有这么简单。
“枢密”这个词拆开:“枢”是中枢的枢,“密”是机密的密,枢密就是中枢的机密。在宋朝,凡是和军事相关的事务,上到战略规划、兵马调发这样的军政大计,下到武官选任、兵籍管理、武器修造这样的琐碎事务,都归枢密院管。那宰相跟它是什么关系?请注意,是平行关系。宰相掌管民政,枢密使负责的枢密院掌管军政,两个机构合称“二府”。外加一个掌管财政的三司使,宰相的权力其实是被一分为三的。
所以,大家很容易得出结论:你看,跟唐朝相比,宋朝皇帝鸡贼吧?把宰相权力分割了吧?宰相权力一小,皇权就一家独大了吧?
这么说,也有道理。但这是事后看的视角。如果我们随着历史进程,亦步亦趋地跟着看,会发现事情正好是反过来的。
这就要说到唐朝安史之乱了。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是整部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看宋代的很多事,都要回到这个节点。

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唐朝皇帝发现,局面太难了,地也少了、钱也少了、兵也少了,更重要的是,谁也信不着了。对啊,老李家过去就是因为太相信安禄山这样的边关大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啊。不信宰相,也不信大将,那该用谁呢?四处一看,嗯,好像能信的人,就是我身边的这些人了,谁啊?宦官。这就是唐朝后期宦官之祸的缘起。咱得明白这个先后逻辑关系,不是宦官先欺负的皇帝,是皇帝先信任的宦官。
唐朝设立枢密使,就是任用宦官干预朝政的关键一步。不过,刚开始完全看不出什么有什么权力,也就是一个传达室,三间房,存放点文件,宦官宫里宫外跑个腿递个信儿。枢密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负责重要信息的上传下达。
但是,这里有一个社会经验,就是永远不要小看那些在权力身边负责传递信息的人。时间一长,这个职位上的人本身就有权力。枢密使的演化也是这样,渐渐地,跑腿的就变成了拿主意的人。你想啊,到了晚唐的时候,皇宫的传达室,也就是枢密院的宦官,拿出来一张条子,指挥宰相做这做那,你怎么知道这是皇帝的意思,还是那个传达室大爷的意思?只要分不清,那枢密使的实际权力就渐渐地要凌驾在宰相之上了。
到了五代,后梁太祖朱温把宦官这个群体一锅端,全部杀掉,那枢密院这个机构是不是就没了呢?不会的。一个机构的存在,不是依靠哪一伙人,而是附着在一个时代的权力结构上的。只要皇帝不信外朝的大臣,想要用自己信任的人,以内制外,那枢密院就有必要存在。那没有了宦官怎么办?有的是人。比如皇帝在即位以前的发小、战友、亲随故吏、藩邸旧臣,只要是和皇帝个人之间有信任关系的人,就行。
五代乱世,枢密院其实还变得更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天天打仗呀。梁唐晋汉周,说是朝廷,本质上就是暂时最得势的军阀。打仗嘛,胜利第一,效率第一,上下之间的信任就变得尤其重要,所以,枢密院权力越来越大。皇帝指示自己的小弟,去,把什么什么事儿办了,这效率多高。其他什么朝廷的体制、用人的公平、社会的观感、长期的稳定,一切都顾不上了,先保证能高效率地把眼前的仗打赢啊。这也顺便就解释了,为什么枢密院后来变成了专门主管军事的机构?因为它的底色,就是一个享有皇帝充分信任的战时体制。它就是为战争机器而生的。
好了,枢密院权力最大,那宰相呢?五代的时候,朝廷也设宰相,但那个时候的宰相只是朝廷的门面而已,干干文字工作,帮着起草个诏书,主持个典礼什么的。比如,冯道就说,自己做过三次宰相,第一次做宰相,有资格任命六部郎中级别的官员;第二次做宰相,权力小了点,只能任命拾遗、补阙这样的台谏官;等第三次做宰相,他的权力更小了,就只能任命一些州县官了。所以,五代时期选拔宰相的标准也变了。只要你是唐朝时候的名门望族,我管你有没有能力,来,到我这里做宰相。个别皇帝选宰相的方式更可笑,抽签,谁抽中谁当。说白了,宰相不重要。
那好了,请问:如果你是宋朝的皇帝,你好不容易结束了五代乱世,削平群雄,现在你想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国家,你搞制度建设的方向是什么?对,恰恰不是削弱宰相的职权,而是要逐步地恢复宰相的职权。
那继续沿用枢密使不行吗?不行。枢密使的本质,说好听的,是皇帝信任的人,说不好听的,就是皇帝的私人,让这样的职位成为国家正式制度的最高职位,会严重削弱政权的合法性。
在古代中国,就算皇权最大,一个正常的朝廷还是要表现出公共性。一个政权的最高职位的担任者,要么符合天下公认的某个任职标准,比如血统、威望什么的,要么就是开放的,我一个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努力向这个职位奋斗。如果皇帝说,不行不行,那样上来的人我都信不过,就是我看谁顺眼我就用谁,那,你皇帝就不是什么“天下共主”,你不过就是个戴皇冠的山大王而已。
直到宋朝,这个问题才有机会解决,就是把枢密使的权力还给宰相,让朝廷有更多的合法性和开放性。
方向虽然明确,但真要操作起来,还是非常难。搞机构改革,可不像搭积木,按照设计图这么、这么搞两下就行。因为信任困境还是摆在那里啊。皇帝要干点事,比如打仗,本能上还是想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啊。所以,重建宰相权威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渐进过程。
宋太祖的办法是,干脆用最信任的人当宰相。宋朝是960年建立的,宋太祖最信任的幕僚赵普,刚开始是放在枢密院的,这符合枢密院的传统,最放心的小弟在枢密院。但是到了964年,太祖把从五代后周留任下来的几个宰相拿掉,任命赵普当宰相。你看,从晚唐时期算起,这是隔了100年啊,宰相终于成了一回实权派。
但是请注意,赵普虽然是文臣,但是严格地说并不算文人,不是进士出身嘛。所以,赵普当宰相,宰相是有权了,但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并不是众望所归的人。但毕竟有了进步。
这是第一步。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开始进行第二步:培养真正的士大夫宰相。
像吕蒙正、张齐贤,他们既是宋朝自己录取的进士,又被宋太宗提拔到了宰相。那宋太宗自己信任的人呢?继续放在枢密院里啊。比如王显、柴禹锡。就拿这个王显来说,他在枢密使的职位上总共干了8年,非常受重用,但他是一个几乎没读过书的人。有一次,宋太宗还安慰他呢,你自己虽然没上过什么学,但是你家祖上还是读过书的。你今天都混到这么高的位置了,让你博览群书呢,确实也为难你。这样,你就熟读《军戒》三篇,就三篇文章,你就不至于遇到事情一无所知了。你看,就这么个不学无术的人,照样可以执掌枢密院,因为这个机构最需要的不是能力,而是信任。这就形成了一个局面:宰相用士大夫,枢密用皇帝自己的人,两条腿走路。这是第二步。
宋太宗时候,其实还走了第三步:开始启用士大夫主管枢密院。有人统计过,宋太宗用过的枢密使,正的、副的都算上,有35人,其中文臣士大夫出身的占了21人。比如石熙载,还有我们大家都熟的那位寇准。渐渐地,文臣掌控枢密院就成了一个惯例。
其实后面还有第四步,就是让宰相也能插手枢密院。名义上,军事上的事儿都归枢密院管,但实际上,到了宋真宗的时候,比如澶渊之战,皇帝完全是和宰相毕士安、寇准商量军事,当时的枢密使叫王继英,基本没有什么存在感。接下来这几十年,如果真有战事,宰相肯定是参与意见的,甚至什么招兵、裁兵之类的事儿,皇帝也是直接和宰相讨论。枢密院的边缘化,是贯穿了整个宋朝的一个趋势,到了南宋的时候,也别费那个劲了,干脆,宰相兼任枢密使得了。到了这一步,把权力还给宰相的任务才最终完成。
我这么一捋,你明白了,为什么欧阳修、范镇这些人,提到狄青当枢密使就痛心疾首。本来,到了宋仁宗这个时候,就算有武人担任枢密使,就算他级别不低,但是他在朝政中是一点存在感都不能有的。有一次,文官宰相在一起蛐蛐皇位继承人这样的大事,根本就不让枢密使知道。当时的枢密使叫王德用,就是武人出身,王德用抱怨了一句,“哎,我就是个泥菩萨,你们也不能当我不存在吧?”结果欧阳修听见了,马上就回了一句:“一个武官老头能知道什么?”你看,当时的武人枢密使,就是这个地位。
好了,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狄青当枢密使,又有军功,又有人望,还有皇帝的信任,那士大夫们会怎么想?这不是歧视武人的问题,这是此前将近100年的改造枢密院的努力要不要前功尽弃的问题,也是大宋朝逐步回归正常政权的进程是不是走了回头路的问题。那你想,大家能不玩命反对吗?一个野兽好不容易被关进笼子里,哪里有再放出来的道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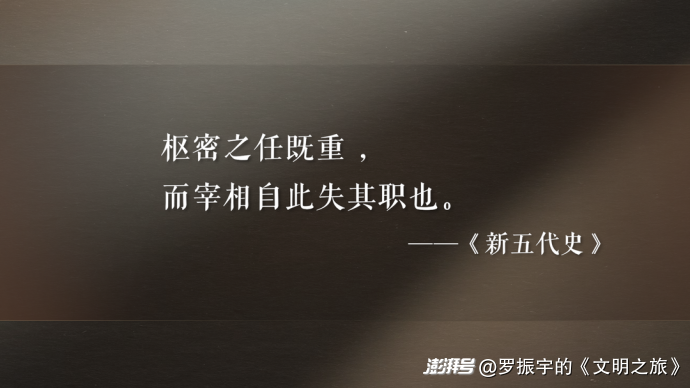
武人狄青
士大夫们为什么不放过狄青?我们刚才交代了宏观上的背景。但这里面还有一个疑点。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今年是狄青担任枢密使的第四个年头了呀,他在公元1053年平定了侬智高的叛乱,然后就当上了枢密使。那难不成,士大夫们围攻狄青,一直持续了四年?
其实并没有。虽然提拔狄青当枢密使,一开始文臣们也反对,但仁宗皇帝态度非常坚决,也就成了。这之后的四年,这事好像就被忘了,狄青的存在感也很低,史书上都没记载这四年狄青到底干了个啥,可能就是个按时打卡上下班,无功无过。那为什么四年之后,欧阳修、范镇这些人,又突然开始集体围攻狄青呢?这就得看看这一年的背景了。
就在今年的正月初一,百官进宫朝贺天子。天子就坐,面前的那个帘子徐徐升起,突然,宋仁宗感到一阵眩晕,帽子都歪了,旁边的人吓得,一边赶紧把帘子放下来,一边掐他的人中,好歹缓过来了。你一听就知道,不好,这明显是中风的症状啊。
到了大年初五,仁宗宴请辽朝使者,宰相文彦博端着酒,到仁宗跟前祝寿,仁宗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不高兴吗?”文彦博知道他病了,这话也没法答。这一天的宴席也只能是勉强应付到结束。第二天,正月初六,仁宗的病情就加重了。辽朝使者要回国了,仁宗给他们饯行,结果使者刚到大殿前的院子里,仁宗就嚎了一嗓子,说快点把辽朝使者召过来,朕差点就见不到他们了!言外之意,是有人要害他,他侥幸躲过一劫。下面的人知道仁宗又犯病了,赶紧扶走。文彦博只能打着仁宗的旗号,糊弄辽朝使者说,皇帝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就不陪了。
连续这么几出,大臣们心里有数了。这个状态,和他爸爸宋真宗最后几年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看来,这是又快到皇位交接的时刻了呀。要知道,大宋朝快100年了,还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皇帝眼看不行了,但是没有接班人。宋仁宗这年47岁,还没生出儿子,也没有册立太子。一个虚悬的、没有确定归属的皇位,是会让无数野心家蠢蠢欲动的。暗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凶险在酝酿。
你可能会说,这是不是有点紧张过度了?至于那么邪乎吗?
至于。皇位继承是一个风险非常高的瞬间。在关键时刻,关键人物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你可以设想一种情况,如果朝堂上存在两个可能的继任皇帝的人选,那大家什么心态?只要这个时候选错了边,哪怕只是不太坚决,将来新皇帝坐稳了,我可能就成了图谋不轨之人。所以,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是高度紧张的,关键人物率先选边站,只要态度坚决一点,说话声音大一点,就会引发其他人的羊群效应,只能跟进。一个小小的扰动,是真的会牵动大局的。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引发改朝换代。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周皇帝宇文赟在二十二岁的时候突然去世,然后就是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巧合,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人突然冒出来,成了权臣。这个人第二年就成功篡位,这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所以,后来的史家有一句评价嘛,自古以来得天下最不费劲的,就是隋文帝。
其实,宋朝也差不多。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当了皇帝,是公元960年的事。但是要知道,就在一年前,959年,赵匡胤既不是当时军功最大的军人,也不是职务最高的军人。而后周世宗柴荣一死,一系列的偶然因素,居然就突然给赵匡胤打开了一个机会窗口。
有了这些历史教训放在这里,仁宗的健康状况又是这个样子,随时可能出大事,士大夫们就要问了,谁是最可能成为撬动局面的关键变量?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转头,看向了狄青。
过去关于狄青,我们听到的都是文臣迫害武将的故事。人家狄青功劳又大,人也谦逊守礼,啥也没干,凭什么被你们一帮舞文弄墨的人污蔑?说人家可能谋反?
但你想过没有?我们有可能忽略了狄青的另外一面——他可是在战场上杀出来的将军啊。

我们可以闪回到四年之前,也就是公元1052年,狄青被派往南方平定侬智高之乱。看起来狄青赢得很轻松,一战就搞定了。在此之前,他主要就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狄青在往前线赶路的途中,给朝廷上奏,希望朝廷别向当时越南的李朝借兵平叛。局面已经很乱了,不要再增加不确定因素了。这其实也是一种自信,我就搞得定,不用麻烦别人。朝廷同意了。
第二件事,狄青担心前线将领轻举妄动,一旦兵败,会导致士气受损,所以他在半路上就下令,等我到前线,再开打,我来之前,谁都不许动。但是,广西前线的军官不干啊,等你来了再打,我们的功劳怎么办?就有人带了八千人进攻侬智高,结果大败。狄青听说了,就说了八个字:“令之不齐,兵所以败”,不听军令,怎么能不败呢?等狄青到了前线,马上召集所有将官开会。都来了?不听我军令,结果大败的人也来了?那就别耽误了,说清罪状,就推出去全杀了吧。当着所有文臣、武将的面,一次性斩了32个人。旁观的武将不用说,全都大腿直哆嗦。就连狄青南下之前主持军务的两个文臣,也是相顾愕然,没想到狄青这么杀伐果决。
第三件,狄青随后下令先调拨十天的粮草,这是摆出一副按兵不动的姿态,迷惑敌人。结果,第二天,他就率军昼夜奔袭,抢占了有利地形,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一战击溃了侬智高的叛军。
如果只看历史结果,狄青好像不怎么费劲,只用一个冲锋就把侬智高打垮了。但是,如果你细琢磨这个过程,就会知道,狄青绝不是一个莽夫,相反,他是一个话不多、肯琢磨、心计深沉、善于把握时机的人。不做则已,一发必中。
这是狄青的性格底色,那做人怎么样呢?古代的名将,身上通常都有一种特质,就是爱兵如子,能和士兵同甘苦。自打战国时期的吴起开始就这样。不是有这么个故事吗?说吴起手下有士兵长了个疮,吴起不嫌弃,为他吸吮疮口上的脓。这士兵的母亲是个明白人,听见这事就哭了,将军为你吸疮,那是换你在战场上为他赴死啊。我儿子这回死定了。自古名将都会这一套,用今天的话说,用和部下打成一片,来建立自己的领导力。据说狄青带的队伍,如果遭遇突然袭击,会人人争先地上前打仗,没人敢落在后头。而打赢了仗呢,狄青也不居功,反而要把功劳给下属。这样的将军能不被部下爱戴吗?
这样的爱戴,在军队中看,是好事,是美谈,但是放在整个朝局中看,可就是一桩祸害了。这意味着,军队中的士兵认同的,不是国家,而是主帅。这样的将军登高一呼,是真能把军队忽悠起来干他想干的事儿的。
更何况你想,现在的狄青,可不只是一位打过胜仗的将军了。他还是一位皇帝力排众议,甚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亲自任命的国家军事部门的最高首长,枢密使。你想,这样的狄青,在军队中是不是更有号召力?
《宋史》就记载,说狄青当了四年枢密使,每次出门,小兵们看见就指着他抒发自豪感:看,这是我们的狄大帅。别的不说了,就说他当了四年枢密使,士兵们每次领到国家发的钱粮,会怎么说?会说,这是我家狄爷爷赏的。
一个将军,要地位有地位,要威望有威望,就这份儿在军队中的号召力,他要真的想干点什么,还真就有机会。他自己即使什么都不想干,有人想干点什么,这也是一支要争取的,不容小觑的力量。
政治博弈就是这样,并不需要每一个参与者都具体做点什么。有时候,只需要你一个态度,就足以撬动大局了。
你可能会说,咱们不能这么聊天。人家狄青好好的一个大忠臣,什么也没干,你们就这么恶意推测。这是混淆了一个人的能力和意愿啊。一个人具备了抢劫的能力,你就把人家当抢劫犯对待,这不是污蔑吗?
是的。类似的对话,在宋代也有一次。
文彦博建议宋仁宗,要把狄青的枢密使免了。宋仁宗说,人家没有罪过,咱就惩罚人家,合适吗?而且,狄青是个忠臣!文彦博说,那你老赵家的太祖赵匡胤,岂不也是后周皇室的忠臣吗?但是结果呢?赵匡胤想不想干什么不重要。君不见陈桥兵变吗?只要咱们太祖得了军心,受士卒的爱戴,到了黄袍加身的时候,由得了太祖吗?
听到这里,宋仁宗只好默然。读史料读到这里,我虽然也知道狄青冤枉,但是,我也只好默然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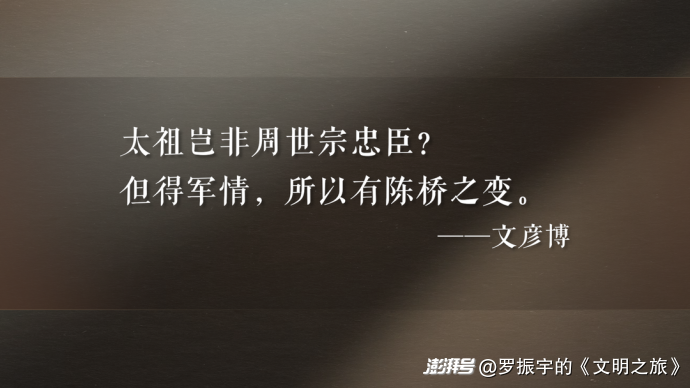
英雄狄青
狄青没有什么错,但是,他必须离开枢密使的位置。这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就像今天,一包火柴没有什么错,但它也必须离开加油站。
这个逻辑很残酷啊。
我们这代被考试训练出来的人,会有一个幻觉:我没有犯什么错,所以就不该承受什么厄运。经常听见有人质问命运: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如何如何,我有错吗?其实,历史车轮不太关心每个人的对错,它只是在挡路的人身上轰隆隆地无情碾过。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说下大天来,狄青落到那样的下场,朴素的道德直觉还是让我们觉得不舒服。
那就追问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我们觉得不爽?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多少还是觉得,欧阳修、范镇、文彦博这些士大夫小题大做了。宋朝建国都快100年了,搞了那么多崇文抑武的制度建设,一个狄青,就让他当枢密使,也是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放在那个位置上,只是做给天下看,国家不会亏待功臣。哪儿还真会对造反?
如果这么想,那我们可能还是低估了英雄在历史中的作用。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思维太过理性。我们总觉得,做成一件事,总是因为方法对了。但其实,在真实历史中,很多事之所以能成,不是因为方法对了,而是因为人对了。这就是英雄。
汉武帝的时候,想要在四川做点事,四川当地的父老乡亲觉得这事儿异想天开,不可能,所以不配合。这态度惹恼了一位四川人,谁啊?司马相如。他写了一篇文章跟大家辩论,里面有一句千古名言,“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说白了,就是不要不信邪,就是有当今圣上汉武帝这样的非常之人,然后就能做成非常之事,就能成就非常之功。不要用普通人的常理,来揣测英雄的可能性。
在创业圈子里,大家也都知道这个道理。在看起来此路不通的地方,就是有人经常能把事情做成。记得有人跟我介绍一位创业者,说就像面前有根独木桥,别人还在买装备、做训练,准备过桥的时候,这位来了,踩着高跟鞋,看都不看就从独木桥上过去了。等她过去之后你问她,过桥有什么经验,她说,啊?哪有什么桥,没看见啊。这就是商业上的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事。
虽然我们并不提倡英雄史观,但这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侧面: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机缘下,就是会决定性地推动历史进程。
你就想中国北方,长城外,草原上的风吹了几千年,那里人的生活方式变化也不大,社会结构也不复杂。但是,每过几百年,大草原上就会诞生一个像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那样的英雄,他们会把散落在广袤草原上的部落整合起来,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像鞭子一样抽打欧亚大陆边缘上的其他文明。草原上的英雄,就像是一把野火,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只要来了,就是燎原之势。

这个草原,其实也是战场的隐喻。有人问过一个问题,说军校培养的是什么人?答案是连长、排长,军队的基层军官。那将军和元帅谁培养呢?只能靠战场。仗打完了,最后赢的人,就是战场筛选出来的将军和元帅。
是的,只要是讲究效率和结果的地方,比如商场和战场,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拦得住英雄的崛起。
说到这里,你再回头看欧阳修、文彦博这些士大夫在做什么?他们不是在欺负英雄,他们只是不肯低估英雄啊。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关于狄青的故事,我们本能地觉得不爽?
其实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我们内心深处,本能地喜欢英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喜欢听英雄的故事。
但是请注意,我们在听英雄故事的时候,我们代入的,可都是英雄本人,而决不会是乱世中的普通百姓。六神磊磊写过一篇文章,他就说,千古文人侠客梦,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梦想,但如果我们真的生在武侠小说描述的那个世界里,会怎样?我们大概率不是郭靖、萧峰、令狐冲,我们极可能是大侠们的剑下亡魂。有英雄的世界,真的适合我们这些凡人吗?

所以,我们不仅要像欧阳修他们一样,警惕英雄出世。更重要的是,警惕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对英雄的热爱。
关于狄青,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场面。
话说,狄青曾经是名相韩琦的手下。有一个军官犯了事,韩琦要杀他,狄青跑去求情,说,这个军官有军功,是个好男儿。韩琦说,这种人算什么好男儿!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也就是中科举的人,才是好男儿!说完,当着狄青的面,斩了这个军官。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个少年,当时气炸了。有这么不讲理的吗?舞文弄墨的秀才,怎么跟征战沙场的人比谁是好男儿?
后来年岁渐长,我知道了,这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好汉观”。都有道理。
第一种好汉是梁山好汉。还记得当年读《水浒传》,看李逵大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觉得他这是真性情,赞。他杀得痛快,我看得痛快。但最好,他活在宋朝,我活在今天。他杀人,不要溅我一身血。
而另一种好汉,就像韩琦说的,科举选拔出来的状元,或者按照既定社会规则,通过自我奋斗而决出的胜利者。当这种人被看成是好男儿的时候,戏剧性、观赏性虽然差了很多,但是,这才是我愿意活在其中的时代。
好,这就是我在公元1056年为你讲的悲情英雄狄青的故事,通过他,我们能看到英雄故事的另一面。
明年,公元1057年,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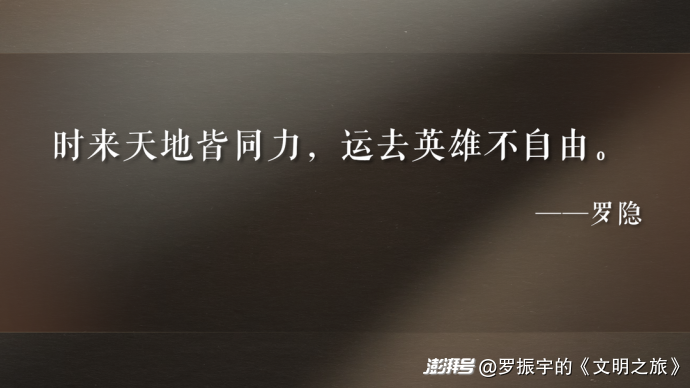
致敬
本期节目我们说的是英雄狄青,先给你读一段元杂剧里描写狄青的曲子吧——
这红抹额似火霞飘,金面具威风赳。
大杆刀轻轮在手,平定了乾坤四百州。
施展你那武艺滑熟,统戈矛。有一日建节封侯,恁时节方显男儿得志秋。
则我这气冲着牛斗,胸怀锦绣,我则待播清风万古把杯留。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自然界里一种特殊的树木——巨杉,它能长得100多米,差不多有三十多层楼高。要知道,这个高度,已经超出了一般树木的生长极限。那它为什么能长这么高呢?因为它会故意吸引雷电劈自己,这样就能引发大火,清除周边的树木、小草,同时为自己的种子发育,提供养料和空间。那它自己不怕雷劈火烧吗?不怕,因为在漫长的生物进化中,它的树皮进化得很厚,而且里面富含防火的化学物质。所以,你看,巨杉看起来高耸挺拔,但它的背后其实隐匿着一段非常残忍,非常可怕的故事。
英雄何尝不是巨杉,它虽然也经受苦难,也艰苦卓绝,我们今天小心翼翼地触碰这个话题,不是想否定英雄,我只是不断地提醒自己,在膜拜巨杉的时候,也要留出一丝念头想一想:万一,我就是巨杉脚下的灌木或小草呢?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
(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宋)王铚撰,朱杰人点校:《默记》,中华书局,1981年。
(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
(宋)王称撰,孙言诚等点校:《东都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
(宋)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中华书局,2015年。
(宋)吴曾撰,刘宇整理:《能改斋漫录》,大象出版社,2019年。
(宋)曾慥编,赵龙整理:《类说》,大象出版社,2019年。
(宋)王大成撰,储玲玲整理:《野老记闻》,大象出版社,2019年。
(宋)彭口辑,孔凡礼点校:《墨客挥犀》,中华书局,2002年。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王永平:《论枢密使与中晚唐宦官政治》,《史学月刊》1991年第6期。
贾宪保:《论中晚唐的中枢体制》,《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唐史论丛》1987年第1期。
李鸿宾:《唐代枢密使考略》,《文献》1991年第3期。
袁刚:《唐代的枢密使》,《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戴显群:《唐代的枢密使》,《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黄楼:《从枢密使到枢密院——唐代枢密使演进轨迹的再考察》,《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杜文玉:《论五代枢密使》,《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
李鸿宾:《五代枢密使(院)研究》,《文献》1989年第2期。
董恩林:《五代政治体制考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戴显群:《五代的枢密使》,《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
曾维君:《唐后期至五代枢密院之演变略考》,《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王瑞来:《论宋代相权》,《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载中国宋史研究会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
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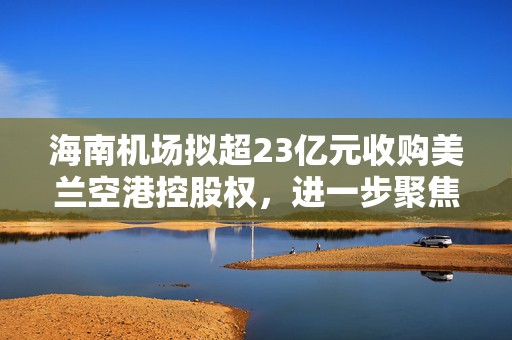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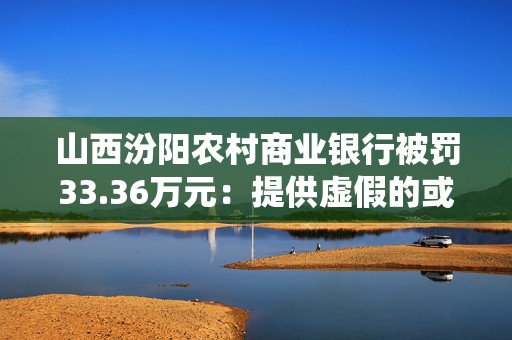





发表评论
2025-05-01 05:10:48回复
2025-05-01 07:57:11回复